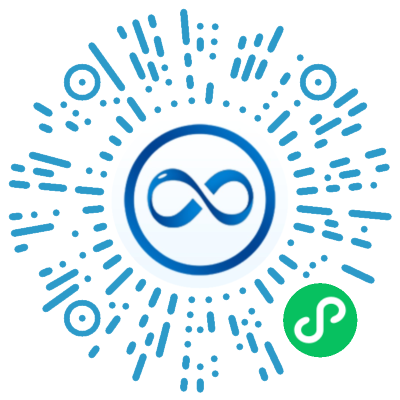松江是“上海之根”,“松江棉布”泛指松江及其附近地区出产的棉布,相关纺织技艺已于2023年入选松江区非遗名录。
江南地区民间历来盛传“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明代中叶,棉纺织生产已成为松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所产布匹通过漕运销往全国各地,乃至东亚、南亚、欧美等地。“松江棉布”有怎样的西传历史?“松江棉布”与海上丝绸之路有怎样的紧密联系?“松江棉布”如何见证千年前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上海外国语大学非遗记译与传播中心负责人、西班牙语专业老师张礼骏,对此进行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松江棉布”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
张礼骏:宋元以前,棉花也称作木棉、吉贝,早年在新疆、云南、海南等地种植,后经闽粤于宋末来到江南。自此,棉花种植及棉纺织业以松江地区为核心向周边地区扩散。然而,元初松江府的纺织技艺较为原始,织造效率低,后经黄道婆将海南黎族纺织技术带回乌泥泾,新式的轧棉“搅车”、竹制绳弦弹弓和三锭脚踏纺车自此诞生,黎汉融合的革新技术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高速发展。《南村辍耕录》中有相关记载:“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
纺织工具与技法的改良同时也推动了松江棉布品质提升。至明清时期,松江棉布已有四大系列:三纱棉布、番布、混纺布和药斑布。我们熟知的飞花布、三梭布、尤墩布、云布、斜纹布、丝布都在其列。
到了明代,虽然全国多地棉纺业都兴盛起来,比如河北冀州的紫花布、贵州遵义土布、浙江乌镇布等,但是都不及松江布的品质,因此我们可以在《天工开物》中读到“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明代帝王将相也用松江棉布作衣,根据康熙《松江府志》记载,“明时,御用近体衣,皆松江三梭布”。明清时期,松江棉布不仅在国内享有“衣被天下”的美誉,同时也经过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了全世界。
中新社记者:如今“松江棉布”以何种形式重新融入现代生活?
张礼骏:“松江棉布”从当今行政区划上来讲,是上海市松江区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这是一种相对狭义的定义,纵观历史,原松江府及其棉纺业的影响范围远超现在的地界概念。因此,现在上海、南通、平湖等地甚至更大区域内的棉布文化虽各有特色,但其内部是相通相连的,从而构成了广义上的松江棉布文化,或者说更广层面的棉布文化圈。
今年3月,上海松江布展示馆的传承人携带上海本土的纺车和织布机及松江棉布制作的服饰和文创产品等,走进上海外国语大学,现场向师生们展示“松江棉布”制作工艺和审美价值。体验制布及试穿松江棉布服饰后,学生们纷纷表示,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文化,布艺传统从电视上的纪录片到了校园生活中,收获颇多。
如今,“松江棉布”一方面面临传人缺失减少,织造量极度萎缩的传承困境;另一方面受到新的棉织物形式及西方文化冲击。值得高兴的是,上海各区涌现了一批中青年传统文化爱好者,他们关注非遗传承困境,用自己的方式在青年群体和手艺人之间搭起桥梁,探索创作符合现代人审美方式的非遗文创,赋予传统棉布新时代的活力。三林标布、嘉定药斑布、松江棉布,还有青浦、金山、浦东和崇明等地老布制作的香囊、玩偶、卡套、笔记本、手机套、电脑包、休闲西装等深受大众喜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时尚。
上海外国语大学“非遗记译与传播”团队,自2019年起在中国各地进行非遗项目调研,制作的多语种非遗宣传片境外播放量超百万,译名册上线上海城市形象资源共享平台IP SHANGHAI。眼下,团队启动“松江棉布”非遗项目,重走“黄道婆之路”,关注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传统棉纺织技艺,记录“松江棉布”申遗经历与西传历史,我们希望能促进“松江棉布”历史文化的国际传播。
中新社记者:外国文献中对“松江棉布”的记录有哪些?
张礼骏:16世纪初,大量葡萄牙传教士来到中国和日本,早期对“松江棉布”的记述以葡萄牙语文献居多。曼努埃尔·德里拉在《1549年至1580年耶稣会牧师和兄弟从日本和中国王国写给印度和欧洲耶稣会牧师和兄弟的信件》中,收录了一封傅礼士神父于1577年写的信,其中提到“一些来自中国的白色和黑色的‘康’布”。
《1549年至1580年耶稣会牧师和兄弟从日本和中国王国写给印度和欧洲耶稣会牧师和兄弟的信件》上关于松江棉布的记述。受访者供图
1590年于澳门出版的Um Tratado Sobre O Reino Da China(《中国王国记述》)中,神父杜阿尔特·桑德和亚历山德罗·瓦利尼亚诺记录了另一种类似亚麻的棉花——木棉(gossipina),“这种棉可以制成各种衣服,我们常常会穿,这些衣服也被销往很多地区”。
到了17世纪初,西班牙语及意大利语文献中也出现了关于松江棉花或棉布的记载。利玛窦在《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一书中提到了松江地区盛产水稻和棉花,当地织造的布匹供朝廷使用。西班牙士兵、历史学家安东尼奥·莫尔加在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菲律宾群岛纪事》)中提到,“无论是不是天主教徒,都不佩带武器,穿着特别的衣服:袖口宽、衣服长,用蓝色的‘康’布做成,如果是服丧用的,则是白色‘康’布”。关于“康”布,他用的词是cangan,和葡萄牙语文献中的canga同源。关于canga这一词的词源,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是吴语“江”的发音,近似/k/,指松江布。
明清时期,除了白棉花,苏松地区盛产紫花棉和紫花布。16至17世纪,西班牙人经马尼拉与中国商贾进行贸易,从福建商人口中得知此布来自南京,便将其称为南京布(mantas de Lanquin),这是因为明朝苏松地区在南京(南直隶)管辖范围内。此后,紫花布对外一直被称作“南京布”,19世纪初在英国风靡一时的服饰中,就有紫花布做的裤子。同一时期,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其《华英字典》中做了关于紫花布的词条:“Tsze hwa poo|紫花布:nankeen cloth”。
中新社记者:如今人们在伦敦博物馆看到的19世纪30年代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正是中国紫花布裤子和杭绸衬衫。“松江棉布”有怎样的西传历史?
张礼骏: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中国与菲律宾贸易往来频繁,向吕宋诸岛出口质优价廉的棉布,使得本地居民逐渐放弃土布生产而改用华布,这些布匹中包括松江棉。
英国东印度公司认识、购买松江棉布的历史要晚于西班牙。根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记载,当时英国人发现南京布不容易褪色,质量高于广州织造的棉布,便特地在中国收购南京布。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除了英美两国,还有来自西班牙、荷兰、丹麦、瑞典、法国等国家的商船贩运南京布。欧洲国家上层社会对松江棉布制品的喜爱,在19世纪多部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比如,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写有,“药剂师过来了。他穿一件青燕尾服、一条南京布裤、一双海狸皮鞋、还戴一顶毡帽——一顶矮筒毡帽,真正难得”。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有,“他最讲究的服装,是一条南京布裤,大象腿式裤筒,裤脚由铜丝带扎在脚下”。《基督山伯爵》中的片段,“一个三十一二岁,身穿淡蓝色礼服,紫花布裤,白背心,举止和口音都是英国味的,来见马赛市长”。海涅的诗歌《诸神的黄昏》中写有,“男人们穿上他们的南京裤”。
中新社记者:“松江棉布”与海上丝绸之路有怎样的紧密联系,如何见证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
张礼骏:“松江棉布”见证并铸就了海上丝绸之路在明清时期的发展。18世纪末至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运输的织物主体已不是丝绸而是棉布,可以形象地称之为“海上棉布之路”。“松江棉布”因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海上丝绸之路因“松江棉布”保持活力。
“松江棉布”在菲律宾、日本及欧洲以实物、文字或画像等形式保存至今,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有力证明。“松江棉布”也是一种文化载体,展现了东西方文明特定时期的审美情趣。同时,以其高超的品质受到各地民众喜爱,是东西方文明成功交流互鉴的典范。(完)
受访者简介:
张礼骏,上海外国语大学西方语系西班牙语教师、墨西哥中心研究人员、非遗记译与传播中心负责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历史研究所访问学者、墨西哥学院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访问学者。译有阿根廷作家卢贡内斯诗集《群山自黄金》、墨西哥作家塔布拉达诗集《〈李白〉及其他诗歌》、智利作家塞普尔维达小说《白鲸的故事》等作品。